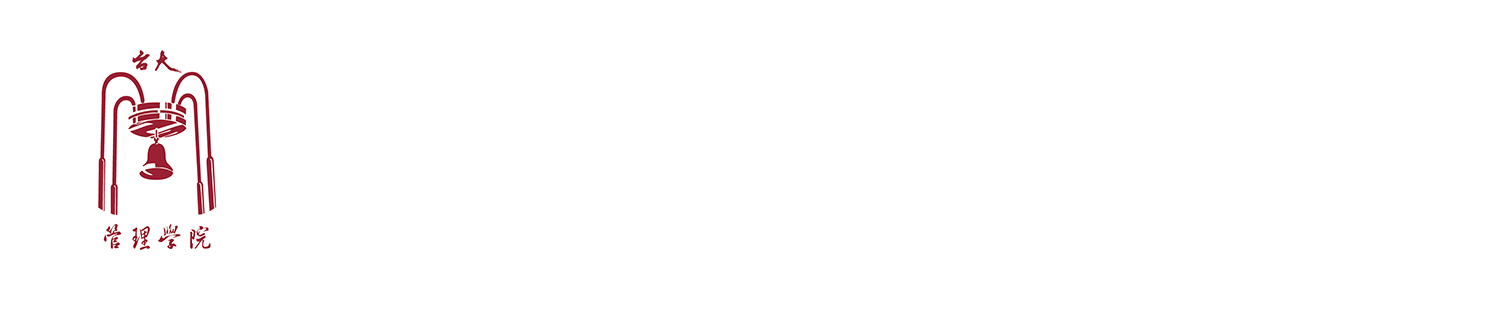財金系同學HEC Paris交換心得
財務金融學系暨研究所
撰文者/財務金融學系 陳品丰
HEC Paris 是法國最頂尖的商學院,在歐洲商學院排名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學校。與 LSE(倫敦政經)、博科尼、ESADE、CBS(哥本哈根商學院) 同屬歐洲頂尖商學院級別,他的MiM在某些指標上甚至被認為是歐洲第一(Financial Times、QS)。在法國,HEC Paris 的地位極高,是那種聽到會「哇!」的那種,學生也被視為比一般大學生更有優勢,屬於典型的 “精英學院”(Ecole)。

然而,與許多想像中的歐美大學不同,HEC 校區其實非常小,不像台大有完整的大學城,而更像是一個郊外的獨立學院,可以想像台大除了管院兩棟外都是森林、草地和學生宿舍。主要的教學大樓只有兩棟,校園周圍環境較為樹林化,沒有太多設施,日常活動範圍其實很有限。如果期待美式大學的 廣闊校園與騎腳踏車通勤的氛圍或是英式古老建築的學院,HEC 可能不符合這種想像,因為他的建築較為工業化,而大部分人也只會(能)在教學大樓、圖書館、餐廳之間行動。
HEC Paris 作為一所法國頂級精英學校,在當地的地位極高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,精英學校在法國社會的影響力與地位相當特殊,甚至可以說是走在路上「自帶光環」的存在。
這所學校的學生組成以白人為主,約有一半是外籍生。從背景來看,大部分本地學生來自上層中產階級(Upper Middle Class),甚至有一部分來自真正的資產階級。然而,最有趣的是,本地生與外籍生之間幾乎沒有交集,兩者的社交圈完全是分開的。
有一次,一位本地生分享說,他們其實瞧不起外籍生,原因是他們認為自己花費極大努力才通過艱難的考試進入 HEC,而外籍生卻能相對輕鬆地透過交換或國際生途徑進來。這讓我聯想到台灣有些人對僑生或特殊招生制度的偏見,這種「學術菁英 vs. 外來者」的心態其實在世界各地都存在。另外,本地生也會歧視從外國回來的法國學生,認為他們在國外讀書、沒有經歷過法國嚴苛的教育體系,因此「不夠格」。這使得 HEC 內部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分層文化。
至於交換生,因為 HEC 交換名額有限,能來的通常都是各國頂尖名校的學生,也因此形成了一個高端富二代聚集的小社群。我經常聽到同學討論要去買 Chanel、Dior 或 Gucci,或是隨口提起父母要來巴黎洽談生意。簡單來說,這群人幾乎都來自一個「不用擔心錢」的階級,出國、購物、旅行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。
但有趣的是,這些人雖然大多家境優渥,但並不只是「富二代」,他們確實各有其長處。如果將這群學生比喻成遊戲中的角色,他們的技能點明顯與台灣學生不同。法國學生普遍擅長思辨,能在討論中快速組織語言並表達觀點,具備很強的說服能力,這點在課堂討論和辯論中尤其明顯,而與台灣學生相比,這些學生特別突出的一點是——外向、積極且自信。這種自信不只來自於語言能力,更是一種從小被訓練的表達能力。即便他們的論點不見得嚴謹,他們仍然敢說、敢表達、敢爭取,這與台灣學生較為內斂、傾向於不出錯的思維模式形成強烈對比。此外,他們的精力旺盛程度也讓人驚訝。很多同學的社群媒體更新頻率驚人,彷彿每天都能產出大量的貼文與限動,甚至有人對夜店文化極為熟悉,這與台灣學生相比,確實是很不一樣的生活方式。
但話說回來,他們的學術表現並不見得比台灣學生更優秀。在小組報告與作業中,我發現這些來自世界名校的精英學生,品質參差不齊,不一定比台灣學生做得更好。台灣學生雖然在表達能力上較為內斂,但在做事的細緻度與報告的完整度上,反而有時候更勝一籌。只是台灣學生常常因為不擅長表達,而顯得比較沒存在感。
剛到法國時,我明顯感受到生活節奏的落差。或許是因為剛從台灣的實習環境與台大的高壓節奏(老實說我應該也相對低壓了)轉換過來,讓我一開始對法國的行政效率感到極度不耐。無論是行政體系的回覆、宿舍維修的安排,甚至房屋補助的申請,所有事情都需要漫長的等待——一封回信可能要一個半月,宿舍的維修可能要一週,讓我不禁回想台灣的便利與高效,例如看完病立刻能拿藥、24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,任何事情都可以「馬上處理」,一切井然有序。
這樣的環境轉換,讓我剛開始有點焦躁,總覺得事情應該要立刻解決,因為從小被灌輸「拖延是不好的習慣」。但隨著時間推移,這種緩慢的節奏開始影響我的思維,讓我慢慢學會不必執著於所有事情都要「當天完成」。當社會環境本身沒有那麼急迫時,你也不會被逼著要求自己時時刻刻都要高效運行,反而能順應這種步調,讓自己放慢下來。
我開始意識到,或許這種心態正是所謂「工作與生活平衡」的關鍵。在台灣,這個詞彙常被討論,卻很少真的有人能做到,畢業後進入職場,工作幾乎成為生活的主軸。然而在法國,我實際感受到這種平衡的存在——當然,撇除行政效率低落的問題。
台灣的工作文化偏向「顧客至上」或「責任至上」,我們習慣無條件地完成交付的任務,哪怕需要犧牲個人時間,甚至覺得這是一種責任感的展現。然而法國人的態度不同,他們的節奏較慢,更關心「這是不是我該做的」,工作與私人生活之間的界線更為分明。這種文化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更寬鬆,也少了那種過度要求的壓迫感。
剛開始,我以為這是一種冷漠,但後來才發現,這其實是一種「恰到好處的距離」。當不被迫追求極致效率時,反而能更自在地面對工作與生活的關係,而回到台灣反而覺得雖然的確方便,但無形中也有一種壓迫感。
剛到歐洲時,最直接的感受就是「人怎麼這麼少」。親身來到歐洲,才發現這裡的環境與台灣的擁擠程度有著本質上的差異。在台灣,無論是在人行道、騎樓、還是過馬路時,總是需要閃避機車或是與其他行人擦肩而過;但在歐洲,即使在大城市,也很少有這種需要與人「搶空間」的感覺。
這種「寬敞感」與他們完善的公共建設密切相關。歐洲幾乎不會出現沒有行人道的路,無論是市中心還是郊區,都有完整的人行空間,完全沒有台灣那種「機車、人車爭道」的情況。這不只是人口密度不同造成的,更多是行人優先的思維,讓道路規劃更符合人的需求。在歐洲,過馬路時,只要有過馬路的意圖,車子幾乎都會主動停下來,而不是像台灣那樣,非得你踏上斑馬線,車輛才願意讓行人通過,甚至有時候還要邊走邊閃車。
當然,這種對行人的禮讓也帶來了一些反面影響,比如在許多歐洲大城市,闖紅燈幾乎成為一種常態,尤其在巴黎,紅綠燈更像是「參考用」,只要沒車,行人幾乎都會直接穿越馬路。這種交通文化的對比,讓我覺得歐洲在「以人為本」這件事上確實做得比台灣徹底,但某些規範的鬆散度也與台灣大不相同。
當然,歐洲雖然有許多優勢,回到台灣後也能更深刻體會台灣的獨特便利性。無論是便利商店、24小時營業的餐廳,還是春節期間依然能買到大部分日用品的便利程度,這些都是歐洲難以比擬的。在巴黎,即便是大城市,許多商店在晚上或假日仍會關門,這對於習慣「隨時都能買到任何東西」的台灣人來說,確實需要時間適應。
此外,台灣的人情味也相對濃厚。或許歐洲的「人際距離」帶來了更自由的空間感,但回到台灣後,確實能感受到更多主動幫助與友善,這也是台灣社會的一大優勢。